名声岂浪垂
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,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;有了伟大的人物,而不知拥护,爱戴,崇仰的国家,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(郁达夫《怀鲁迅》)
那么,我们是怎么对待我们民族的伟大的人物的呢?
表面上敬重他,仰望他,实际上把他符号化、脸谱化。
长期以来,很多人心中的鲁迅大概是这样的:外形么,瘦,个子不高,短发根根直立,胡子修剪成隶书“一”字,长衫。神情严肃,目光坚毅,或站或坐。手指夹着点燃的烟或拿着毛笔,或者一手夹着点燃的烟一手拿着毛笔。——课本上是这么画的。
成就么,他很厉害,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。写了很多杂文,像投枪,像匕首,批判国民劣根性,怼遍天下无敌手。——课堂上是这么分析的。
畏惧他,不愿亲近、理解他。
他的文章好难懂,“不明觉厉”,再加上让人眼前一黑的“熟读并背诵第某段到第某段”……哎呀!打扰了,告辞。
利用他。
每隔一段时间,某些媒体就要拿“鲁迅作品退出语文课本”炒作一番,然后群众或呼天抢地“不能够哇”,或拍手称快“早该如此”,最后媒体“调查”后称“此乃假消息”。循环往复。
调侃、恶搞他。
“我有两个哥哥,一个是男的,还有一个也是男的。”“鲁迅:这话我没说过。”
诋毁、攻击他。
不知从何时开始,一种无知无畏的风气悄然盛行:“孔子有什么了不起的?”“《红楼梦》有什么了不起的?”“××有什么了不起的?”
所以,鲁迅有什么了不起的?文章晦涩难懂,凭什么有那么高的地位?或者,套路少一点,直接戳破窗户纸:
鲁迅是因为政治因素才被捧得这么高的吧?
确实,鲁迅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他个子不高,而且内心没强大到对此毫不在乎的地步。至少在某一瞬间,他对此是有点介意的。1933年2月17日,他见到了来华的英国文豪萧伯纳。
午餐一完,照了三张相。并排一站,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。虽然心里想,假如再年青三十年,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……。(《南腔北调集·看萧和“看萧的人们”记》)
身高被人比下去,有小情绪了。
其实,他与身材高大的萧伯纳合影,气场丝毫不落下风,有照片为证。
个子矮有什么关系,主要还是看气质!
他也没有那么无畏。
看到流血牺牲,他会恐惧;上了黑名单,他会离家避难。他不是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,以身殉道的谭嗣同。
但是,他会无私帮助青年,直到对方现出中山狼的原形,露出獠牙狺狺而吠;会在明知有性命之虞的情况下,不带钥匙去参加杨铨的追悼会;会冒险多次接纳瞿秋白夫妇在家中避难,透支自己的健康为亡友出书——虽然那时候他早已没有什么健康可言了。
其实,战士的日常生活,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,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,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。(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“这也是生活”……》)
他的生活很简朴。
他认为,生活太安逸了,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。他希望争分夺秒,有事就赶紧做。他的居室陈设很简单,只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家具。他甚至冬天不穿棉裤,也不睡柔软舒适的床褥。他不在乎衣服上有补丁,连皮鞋都补过好多次。
但是他买书时毫不吝啬,日记里的书账密密麻麻。每月买书花销多则几百元,少的时候也有几十元,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他幼时就有的图书品相强迫症伴随一生,新书到手先包书皮,品相不好就再买一本。他修理线装书也很有办法,走线整齐,有时还加装布面。
与书相关的事,他做起来心灵手巧又有耐心,生活方面却差得远了。
他抡起大锤砸过冬用的煤炭,结果砸伤了自己的手指;他童心大发从高处跳下来,结果崴了脚;他调皮地跳带刺的铁丝网,结果被划了两处小伤;连饭后遛弯他都能踩到松动的地砖摔破膝盖,于是弯也不遛了,委屈巴巴地回去——路上还买了一包点心——涂碘酒,吃点心。
他有心做个负责的好父亲,可又缺乏育儿经验,周海婴被他折腾得不是挨饿就是受冻,连洗个澡都要感冒发烧。他被吓怕了,终于肯退位让贤,请专业的看护给孩子洗澡。虽然请看护要花钱,但求医问药更贵,两害相权取其轻,宁可破财免灾了。
他的身体不算好。
他年轻时就抽烟很凶,晚年更是烟不离手,抽的烟大都很廉价。他常年超负荷工作,吸烟在“提神”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。
他少年时牙就不好,成年后变得更差,自己学医也无济于事,不得不经常去看牙医。治疗的方法无非要么拔,要么补,要么连拔带补。牙齿越拔越少,牙疼却愈演愈烈,终于拔无可拔,只好和全口假牙相依为命。
他牙齿不好,偏偏爱吃甜的,甚至在去看牙医和看完回家的路上还要买糕点糖果。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,还九死不悔。
有一次,朋友送来一包能治口疮的柿霜糖,吃起来滑溜溜、凉丝丝的,他很喜欢。虽然几次三番提醒自己要留一点治将来可能会有的口疮,还是忍不住嘴馋,每次拿出来都开心地吃个不停,终于吃了个精光。一边吃一边安慰自己:总不能为了名正言顺地吃柿霜糖就故意去长口疮吧,如果永远不长口疮,难道就永远不配吃柿霜糖?不如趁着新鲜都吃了算了。
他的家乡盛产黄酒。他喝酒,但酒量一般。刚从日本回国时,他心情压抑,一度喝酒比较频繁,后来也难免有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时候。
他饮茶,也喝咖啡、吃冰激凌。
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,别人打牌、看京剧、逛八大胡同,他全都没兴趣。他不喜欢“冬冬喤喤”“一大班人乱打”的京剧,提到京剧名旦梅兰芳的时候,话说得也很不友好:眼睛凸,嘴巴厚,脸又胖,扮的黛玉像麻姑;“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”。(《坟·论照相之类》)新中国成立后,梅兰芳作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,很少出席鲁迅纪念会,即便到场了也不发言。
在上海时,他经常看电影,频率高的时候几乎每周一部,在去世前十天,他还看了一部苏联电影。像现在的很多观众一样,他看了好片会二刷,会推荐给朋友,看了烂片会毫不留情地吐槽。
他也会有负面情绪,有时候还挺八卦的。
1932年冬,鲁太夫人生病,他北上探视,写信给许广平吐槽:
她(注:鲁太夫人)和我们的感情很好,海婴的照片放在床头,逢人即献出,但二老爷(注:周作人)的孩子们的照相则挂在墙上,初,我颇不平,但现在乃知道这是她的一种外交手段,所以便无芥蒂了。二太太(注:周作人妻羽太信子)将其父母迎来,而虐待得真可以,至于一见某太太(注:朱安),二老人也不免流涕云。(《书信·致许广平》)
此时他已过知天命之年,还是忍不住暗暗为老妈的“偏心”而吃醋,像个争宠的小孩子,可是又自己把自己给劝好了。不知这算不算是一种精神胜利法。弟媳羽太信子虐待父母,他知道了也要悄悄地嚼一下舌根,八卦起来和我辈俗人没什么分别。
他的艺术修养很好。
他小时候就欣赏木刻版画和传统小说的绣像插图之美,还亲自动手描了不少绣像。他描的绣像能找到买主。
在矿路学堂读书时,他绘起图来游刃有余;在仙台医专学医时,他画解剖图都要讲究好看,虽然因为画得不对被藤野先生特意指出,但是藤野先生也承认:确实画得比实物更好看。
他自称书法水平不高,其实他一度在搜集、临摹碑帖方面花过很多时间和心力,字写得不错。有很多出版机构集他的字做报头、社名。
他给自己设计的衣服简洁实用,版型挺括,时至今日看来都不过时。
他亲自画图纸参与改建自己的房子。他设计了北大校徽、中华民国国徽。书籍装帧设计就更多了,《呐喊》《朝花夕拾》《而已集》《奔流》《萌芽》《小彼得》《艺术论》《文艺研究》……
他很早就接触了版画。长妈妈买的《山海经》、为了品相完美而去书店换了一遍又一遍的《毛诗品物图考》,都是木刻版画。虽然前者刻工粗劣,人物眼睛都刻成了方的,他还是无比珍视。成年后,他有意识地收集国内外版画,从画册到原作都有涉及。
收集版画,最简单也最费钱的方式就是买。很多青年版画家求他指教,会把自己的作品寄送给他。有位苏联版画家大概是因为不差钱,提出想要一些中国的宣纸,以纸换画。这有何难?他随后寄去一些宣纸和日本纸,换到了一些原作。各取所需,皆大欢喜。
他晚年致力于倡导新兴版画创作,组织、资助、指导版画社团,出版刊物、画册,多次举办、资助版画展览,还多次撰文,为新兴版画、连环图画摇旗呐喊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他曾经组织木刻讲习会,讲师是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,他亲自做翻译。学员共13人,后来成为中国新兴版画的开拓者。他的坚定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新兴版画运动,他是版画界公认的新兴版画之父。
他读过旧式私塾,读过洋务学堂,读过医学专科,可谓横跨文科、工科、医科。
做中学教员的时候,他根据在矿路学堂学到的知识,与人合编了一本《中国矿产志》,封面上赫然印着“国民必读”四字,作为教材发行。《狂人日记》在他生前就入选了语文课本。所以,他并不是1949年以后才和教材结缘的,是不是把他的作品请出教材,他大概也不会在乎。
他是作者,是编辑,也是学者。
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,会写八股文,还曾师从章太炎,有深厚的小学功底。
古籍校勘方面,他辑录校勘的《嵇康集》是公认的佳本。
他和周作人合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全用文言,若无深厚功底,断难办到。蔡元培说:“周君所译之《域外小说》,则文笔之古奥,非浅学者所能解。”也许这就是销量惨淡的原因之一。试看一例:
临吾上者、有苍天一角、天半见一巨星、灿然作光、益以小星三四。四周何有、为暗为高、此棘丛也。吾卧棘林中、众遗我矣!时觉毛发森然皆立。(《域外小说集·四日》)
简洁、冷峻,有魏晋古文的气息。
他的小说质量极高。圆熟老辣的《狂人日记》有开创之功,自不必说。《阿Q正传》即便放之世界文学之林也毫不逊色。
他的散文数量不多,但质量是一流的。
诗歌方面,《野草》是中国现代散文诗走向成熟的第一个里程碑。他的旧体诗中规中矩,时有警句。《摩罗诗力说》是中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纲领性文献,虽然大多数人都看不懂。
学术方面,《汉文学史纲要》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是研究文学史不可绕过的力作。
杂文更不必说,已然成为了冷兵器。
他这样多才多艺,留下了海量的著作、译作,而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55年。
至于他的据说“佶屈聱牙、晦涩难懂”的文笔,试看以下几条:
少顷大雨,饭后归。道上积潦二寸许,而月已在天。(《日记·》)
谈至十时返室,见圆月寒光皎然,如故乡焉。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。(《日记·》)
夜微风,已而稍大,窗前枣叶簌簌乱落如雨。(《日记·》)
风而日光甚美。(《日记·》)
这些从日记中随手摘抄的记录,寥寥数语,明净恬淡,韵味悠长,宛如小品,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“三五之夜,明月半墙,桂影斑驳,风移影动,珊珊可爱”(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)。
在他写作的时代,白话文尚不成熟,语法尚不规范。他建议中国的年轻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,他本人恰恰已经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书,深厚的旧学功底不知不觉从笔尖流出,使得这话听上去活像气话,没什么说服力。
作家余华曾经在挪威奥斯陆大学演讲,演讲稿整理发表时,媒体取的题目非常标题党:
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。
在演讲中,余华说,在特殊时期,鲁迅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,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。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。他虽然名声达到顶峰,可真正的读者寥寥无几,“鲁迅先生说”只是一个时代在起哄而已。
特殊时期之后,他回归于一个作家,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。很多人继续推崇他,也有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他。
至于余华自己,像很多人一样,他青少年时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的鲁迅作品,从小学读到高中,只觉沉闷灰暗、无聊透顶。
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,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。
没错,很多人至今仍然这样认为: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。
1996年,有导演想将鲁迅小说改编成电影,请余华做策划。于是余华重读鲁迅,第一篇就是《狂人日记》。
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,用了这样一句话:“不然,那赵家的狗,何以看我两眼呢?”
我吓了一跳,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,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。另外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,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,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。
待到读完《孔乙己》,余华立刻给导演打电话:不要糟蹋鲁迅了,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。
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36岁的夜晚:
鲁迅在我这里,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。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,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,我感慨万端,我觉得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,他属于成熟并且敏感的读者。同时我还觉得,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,有时候需要时机。
也许,“周树人”也好,“文言文”也好,学生在心智未成熟的时候早早学习,宛如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人被迫接受武林宗师的全部内力,羸弱的小身板根本无法承受这样慷慨的馈赠,只会在对方排山倒海的内力下吐血三升,一命呜呼。
从这个角度说,鲁迅退出低年级语文课本,有道理。
但是,鲁迅留在低年级语文课本里,也有道理。
金庸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里,张无忌被谢逊逼着硬背武功口诀,死记硬背,没有讲解,背错了还要挨打。十几年后,当张无忌在光明顶念出当年苦背而完全不理解的七伤拳口诀的时候,他完全理解了义父的苦心,并为之庆幸不已、感激不尽。先了解,先背诵,长大了,阅历深了,再慢慢地悟。总会有一部分学生,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,成为理解教材编者的苦心的那个“张无忌”,不可能是全部,但多多少少总是会有的。
至于毁谤……
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他大概也不会在乎。
▼把时间交给阅读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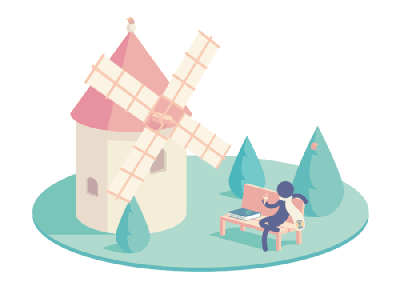






 二、大学城附近会建有广场,基本的娱乐场所都会有。
二、大学城附近会建有广场,基本的娱乐场所都会有。
添加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