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适和徐志摩是朋友,做为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领军人物,他们对白话诗的讨论,见证了那个时代新旧交替时的迷茫与探索。(因为那个时代语言方式与如今区别较大,阅读需要耐心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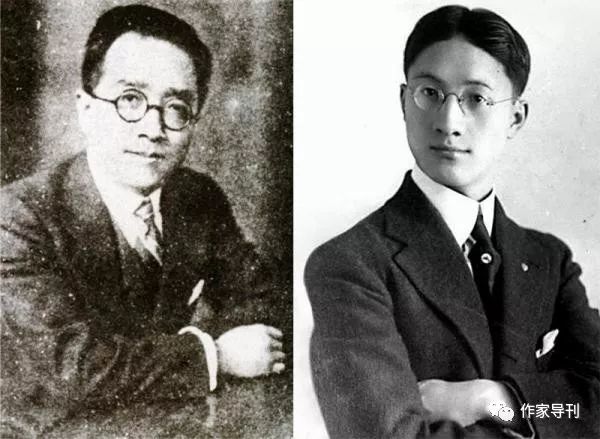
胡适(左)徐志摩(右)
徐志摩和胡适成挚友是他1922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的事。次年十月胡适到上海一趟,常和徐与郭沫若论诗。继而他们几个朋友一起去杭州玩了十天,一起泛舟,游西溪,看日出。率真的徐志摩带出了胡适童稚的一面。胡适写道他们有一晚到了平湖秋月,“人都睡了。我们抬出一张桌子,我和志摩躺在上面,我的头枕在他身上,月亮正从两棵大树之间照下来,我们唱诗高谈,到夜深始归。”
胡适日记上说他读了徐新近写的《天宁寺闻礼忏声》非常高兴:“志摩与我在山上时曾讨论诗的原理,我主张‘明白’、‘有力’为主要条件;志摩不尽以为然。他主张 是一个要件,但他当时实不能自申其说,不能使我心服。十二日我在上海沧州旅馆时,他带了一首《灰色的人生》来,我读了大赞叹,说‘志摩寻着了自己了!’……英美诗中,有了一个惠特曼,而诗体大解放。惠特曼的影响渐被于东方了。沫若是朝着这方向走的;但《女神》以后,他的诗渐呈‘江郎才尽’的现状。余人的成绩更不用说了。我很希望志摩在这一方面做一员先锋大将。”
胡适倡导文学革命,这运动的争论核心是能不能用白话文做诗。据他《逼上梁山》一文说,他和赵元任1915年讨论中国文字为何难教,就认定了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。梅光迪路过康奈尔大学时力驳胡适此观点,愈驳愈激烈,胡适便提出中国文学必须革命。次年任鸿隽与友人在康奈尔附近的湖上摇船,遇风浪船翻了大家湿了衣服,作了一首四言诗寄给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院的胡适,用了几个“死”字,引发胡适去信批评;而在哈佛的梅光迪则替任鸿隽抱不平,给胡适写信说:“……文章体裁不同,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,诗文则不可。”任鸿隽写道:“如凡白话皆可为诗,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?……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,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,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,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!”笔战数月下来,胡适厘清了自己对白话文学的想法,1917年初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了《文学改革刍议》。
胡适于1923年初写了一篇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,说近来白话短篇小说已很有成绩,鲁迅屡有佳作;散文很进步,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;戏剧和长篇小说成绩最坏,因仍没有人尝试。对新诗是这样评估的:“白话诗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。诗体初解放时工具还不伏手,技术还不精熟,故还免不了过渡时代的缺点。但最近两年的新诗,无论是有韵诗,是无韵诗,或是新兴的‘短诗’,都很有许多成熟的作品。我可以预测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。”
此前胡适对个别诗人的白话诗评论相当苛刻:“我所知道的‘新诗人’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,大都是从旧式诗,词,曲里脱胎出来的。沈尹默初作的新诗是从古乐府化出来的……傅斯年,俞平伯,康白情,也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,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……能偶容纳在新诗里,固然也是好事……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——在自然的轻重高下,在语气的自然区分——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……但是读起来自然有很好的声调。”(《谈新诗》,1919)对于自己,胡适说:“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,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在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,虽然一年放大一年,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……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,心里好不嫉羡。”(《尝试集》四版自序, 1922) 然而他觉得那些少年诗人的作品并不成熟:“(汪)静之是少年诗人中最有希望的一个, 又是未免有些稚气,又是未免太露……”(《蕙的风》序,1922)“康白情……受旧诗的影响不多,故中毒也不深……尝试的时代工具不能运用自如,不免带点矜持的意味……山哪, 岚哪/云哪,霞哪……竟成了新诗的滥调了。有些诗陷入‘记账式的例举’……(俞平伯) 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。表现力薄弱,有些偏加上哲学调子的话,画蛇添足。平伯最长于描写,但偏喜欢说理…… Burns并不提倡民众文学,然而他的诗句风行民间,念在口里,沁在心里,不是‘理智化’的诗人做得出的。”(《评新诗集》,1922)
从他具体的评语可看出,胡适理想中的白话诗必须摆脱旧诗的格律,不一定押韵,句子可以长短不一,但读起来必须抑扬顿挫自然动听;既不能矜持,又不能太露;最忌滥调,记账式的列举或太理智化;最好能风行民间,念在口里,沁在心里。这何谈容易!然而徐志摩有几首白话诗达到了胡适的理想!
胡适是喜爱旧诗词的,虽提倡白话诗,要证明用白话也能写出好诗,对旧诗词却仍恋恋不舍。原来徐志摩之所以没有受旧诗词“中毒”,没写缠过足的白话诗,是因他根本不会做旧诗词;对他来说词往往是炫人耳目的把戏。他刻意远离词,害怕沉溺在奇巧纤丽的词藻里自己作诗会矫揉造作起来。
胡适鼓励徐志摩研读宋词,是因他领悟到新诗和宋词有密切的亲缘关系;他也许并没意识到刚刚兴起的留声机所播放的“时代曲”,与新诗和宋词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。他另一位好友赵元任在这方面就比胡适更先进,兴致勃勃地为胡适的白话诗谱曲,也为徐志摩的《海韵》谱曲。刘半农写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经赵元任谱曲后风靡一时。
此后徐志摩和胡适一同办新月书局和《新月》月刊,这里就不必赘言了。
徐志摩1931年尾逝世。那一年,他到北大教英文,和陈梦家等创办《诗刊》季刊,又在北平女子大学兼职。陆小曼不愿离开上海,他只好北平上海两头跑,在北平时借住在胡适家。胡适三月的日记有这么一则:“晚上与志摩谈。他拿T. S. Eliot的一本诗集给我读,我读了几首……丝毫不懂得,并且不觉得是诗。志摩又拿Joyce 等人的东西给我看,我更不懂。又看了E. E. 的 is5,连志摩也承认不很懂得了……志摩说,这些新诗人有些经验是我们没有的,所以我们不能用平常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作品。我想,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特殊经验,到底他们不曾把他们的经验写出来。志摩例举现代名人之推许T. S. Eliot,终不能教我心服。我对他说:‘不要忘了,小脚可以受一千年的人们的赞美,八股可以笼罩五百年的士大夫的心思!’”
如众周知,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时爱上了林徽因,决意和结发妻子离婚;怎知林徽因要接受父亲替她安排的婚姻,嫁给徐志摩恩师梁启超的儿子。徐志摩即把感情转陆小曼,把她想象成完美的伴侣,求胡适说服父亲让自己和离了婚的陆小曼成婚。不料婚后娇生惯养且多病的陆小曼不得公婆意,且染上鸦片瘾,加以徐家财力骤然衰退,两人便不断发生摩擦。
相信胡适为曾替徐志摩追求陆小曼推风助浪是很内疚的。徐志摩十一月飞机失事身亡,他震惊悲恸之余写悼文,重点居然是替死者的第二次婚姻辩护,说:“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。他的追求,使我们惭愧,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,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。他的失败,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……”继而胡适写了一首诗,描述他怎样在书房含泪不忍推开徐志摩心爱的猫,连同一封写给徐志摩却未完成的信,交给《大公报》发表:“我读了《诗刊》第一期,心里很高兴……新诗前途乐观,因为《诗刊》的各人抱试验的态度,这正是我在十五年前幻想提倡的一点态度……梁实秋给你的信(创刊号),我读了颇有点意见……实秋说:‘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’……我当时希望——我至今还继续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,思想,情感的诗……”
胡适在文后附了几句:“收信的志摩已死去二十天了。我今天检看原稿,不忍再续下去了……”他赶紧发表此信,无非要强调徐志摩的“失败”并不能掩盖他在文学上的成就。
没有白话文学,也许就没有五四运动。年轻人能够用现代的语言表达思想和感情,促使他们一下子摆脱了许多旧时文人惯有的思维与习气,加强了对自己感知的信心,新思想才得以迅速地蔓延;即便是鲁迅,也是改用白话写小说才触动到广大读者的。
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,他们事事须自己摸索,而文学是他们在新旧两个世界间一起研讨航线的工具之一。徐志摩之死,对胡适来说,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文坛爱将,更痛失一个同舟共济的伙伴。





 二、大学城附近会建有广场,基本的娱乐场所都会有。
二、大学城附近会建有广场,基本的娱乐场所都会有。
添加新评论